最近,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瀛的新书《开:周瀛的西方哲学课一百次》由上海三连书店/理想国出版。 这本书的内容来自周泸马面向大众的音频课程演讲。 书完成时,他也特意留下讲稿的痕迹。 “因为这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很强的代入感。 希望能提供现场感和对话交流的感觉”。
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不少,不仅要求很强的逻辑思考能力,对西方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,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入门并不容易。 周濂说,至少他得到的听众反馈是这样的。 同时,这样的课程也是老师的考验,周瀛最初低估了音频节目的难度,后来说:“在课堂上老师随时与同学交流,有肢体语言和表情的协助,还有PPT的展示,是多向信息的汇集。 但是,要录制声音,任何噪音和语言都是非常刺耳的。”
不管怎样,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。

周濂
澎湃新闻( www.thepaper.cn )记者就西方哲学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,访问周瀛,采访内容如下。
大众视野与文科界中的西方哲学
新闻:在评论区回复或用语音详细回答问题。 听众自己的哲学知识储备感觉如何?
周濂:很多听众都参加了,不仅在学校,在所有的课堂上都提出了问题。 我也发现了一些特别有哲学才能的孩子。 但是,大多数听众都没有哲学基础,特别是谈论康德,他们非常难以理解,用语变得非常繁琐。 因此,如何平易近人地谈论西方哲学是件很辛苦的事情。
澎湃新闻:法国高中有哲学课。
周濂:是的。 我在人大课上给学生看过法国高中毕业考试的哲学问题,都很专业,想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,要求学生关注哲学史的背景和现实世界。 我认为我们的中学教育在这方面有所欠缺。
澎湃新闻:那么在制作音频节目之前,如何推进其他哲学推广工作是合理的?
周瀛:有几个面向大众的哲学普及讲座。 例如,陈嘉映老师讲了一个很相似的哲学讲座,他的哲学大众很容易接受。 但总体来说,我认为目前国内普及哲学的工作还不够充分。 我认为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 在大众文化市场中,中国的历史一定是最受欢迎的。 因为我们是历史学大国。 相比之下,中国的哲学比西方的哲学更美味,“孔孟老庄”,大家都会说两句话。 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、思维方式、重视逻辑推理论证的特殊性等,对中国人来说还不知道。
澎湃新闻:与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关吗? 曾经的“西学热”也影响了大众文化。
周濂:当时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和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卖出近10万册,但现在已经是畅销书的水平。 这确实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。 购买这些书的人也不一定认真读,但时代以此为时尚。
但是今天不仅哲学,人文学科全体也周边化了。 在大学校园里,人们也很难在日常会话中遇到萨特、加缪、福柯等话题,这些问题已经脱离了大众的视野。 我们当时在上大学,这些都是必读书目,不仅是哲学系,以讲述这些人名和他们的哲学体系为荣。

“存在与时间”
澎湃新闻:那么,现在和文史学家交往时,你感觉西方哲学的边缘化吗?
周濂:我没有这种感觉。 另一方面,我和他们交往的机会不多,另一方面,在我能想到的少数交往中,我觉得他们对西方哲学有着很强的敬畏精神。 文史哲毕竟是共通的,作为专家,深刻认识到西方哲学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所占的重要性。 我感觉不到周边化。
澎湃新闻:现在的文化类媒体也主要关注文史,对西方哲学的关注甚少。
周濂:我想他们也是从与会者的角度考虑的。 毕竟哲学文章读起来很乏味。
澎湃新闻:考证文也很无聊。
周瀛:但对考证感兴趣的读者很多。 例如,知道那样冷门历史的普通读者还很多。
澎湃新闻:哲学和民间都有广阔的基础。 去年世界哲学大会之外有很多哲学爱好者。
周濂:我认为民间哲学家的人数还少于史学爱好者,但可以说是少得多。 此外,中国人学哲学容易进入误区。 民间哲学家的特征是,构筑一个既没有古人也没有来人的宏伟系统,用它来说明世界上的一切。 这是他们对哲学的误读。 解释一切事物的理论存在于古希腊时代,我认为中国的阴阳理论也是从事这项工作的。 虽然现在西方哲学已经放弃了这种宏伟的野心,但很多民间哲学家还在做这样的工作。
澎湃新闻:在美国,分析哲学成为主流。
周濂:是的,哲学越来越专门化,越来越细分。 即使在哲学内部也是隔山般的隔行扫描,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不能真正理解对方在做什么,很多言行和黑话也不能流畅地切换。 特别是最尖端的文章,比如心灵的哲学和分析哲学,如果没有长期的哲学训练和准备,也许是完全看不懂的。
澎湃新闻:西方哲学的传入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可以并列论述吗? 除了宗教因素,前者为什么难以被吸收利用? 因为概念的难度和想法不一致吗? 相比之下,西方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的概念似乎很容易被接受,但象牙塔内也有很多。
周濂:其实很难相处。 如果一定要比较。 首先佛教的传入有很长的本土化过程,中途多次遇到儒教和道教的抵抗,最终本土化了。 而本土化的过程在当时的统治者接受的同时,佛教也为专业的大众提供了安全的思想资源。
我认为西方哲学在本土化方面很难。 首先,我认为在世俗化方面很困难。 因为西方哲学始终是少数精英掌握的语言和思维方式。 把西方哲学放在西方思想的大背景下,它迂回西方的整体文化,是间接的,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。 例如,对事实本身的尊重、对真理的追求、对论证逻辑的强调。 这些和中国现有的思想和文化习惯有不相容之处。
澎湃新闻:那个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吗? 西方哲学的传播时间也不长。
周瀛:当然希望时间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,但时间似乎也不是万能的。 这可能与我们整个语言系统有关。 语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载体。 西方人发展本体论思想,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欧洲语的独特表现有关,因此他们这样寻求“是”和“存在”的概念。 然而,中国人天生对这些问题并不敏感。 因为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视域之外。 但是,对批判性思维和理论的严格追求,强调事实本身,通过教育逐渐普及,深入人心。 但是,这个过程相当长。
澎湃新闻:由于周密的思维和科学精神是共同的,我们还缺乏训练吗?
周濂:一方面是训练,另一方面是数十年或者100年,西方走过500年或者2500年的路,途中缺课真的很多,包括科学精神和公共场合的宽容精神,不能说只靠道理和教育来弥补。 其实在西方社会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和进化,甚至经历了严峻的社会斗争后,才取得的历史成就。 例如宗教宽容发生在30年的宗教战争中,6700万人丧命,使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认识到要接受宗教宽容的价值,是血泪的产物。 科学精神的确立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,很了解伽利略和布鲁诺的境遇。 中国人在这方面走历史的捷径,绕过了某种意义上的必要阶段。 我们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,但并不知道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意思。 我们崇敬科学家,但缺乏科学精神所必需的怀疑精神和真正的意志。 我们习惯于服从权威。 这种权威意识很可能源于中国的传统惯性。 只不过是改变了崇拜的对象。 在现代化进程中,我们作为后发国走捷径从捷径中获利,因此要付出相应的代价,总有一天要重修那些落后的课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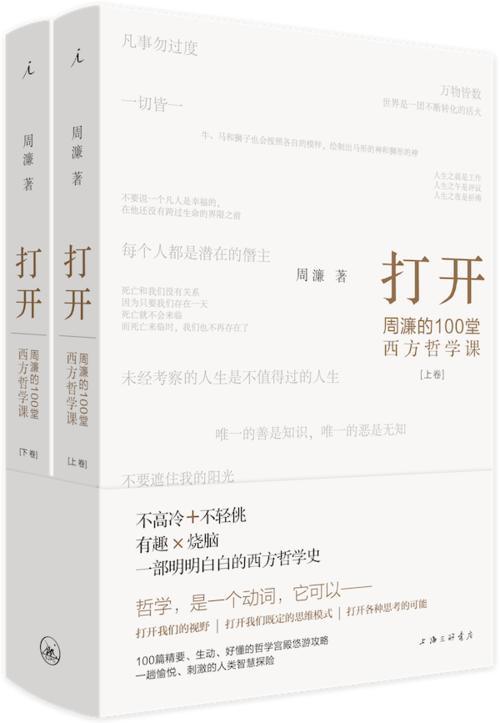
"打开:周瀛的西方哲学课程一百次. "
澎湃新闻:现代文科学术强调的理论性和理论性能在哲学原着的读书中得到吗? 对于一些人文学科,可以像文艺学一样引入西方概念,但在理论的构建和论述方面难以推进,这与哲学训练不足有关吗? 或者与学科专业化有关?
周瀛:一方面是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问题,我认为强行处理西方文艺理论和哲学概念可能会有不恰当之处。 另一方面,你可能会说,如果他们不太了解西方哲学的经过和理论内部的细微概念的区别,最终就像隔山一样,可能会发生问题。 我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优秀的法律学者翻译了政治哲学的着作,他的学问品格无可置疑,但是有很多误译。 这种现象可以像隔山一样充分地解释。 真正进入专业领域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。 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热爱引用西方哲学概念理论,也许是一种时尚。
澎湃新闻:难道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哲学重视问题,复旦哲学偏重哲学史吗?
周濂:我不知道这个说法。 当时我在北大读书时,北大也是哲学史悠久。 中国哲学教室有冯友兰、张岱年、陈来等老师的传统。 西方哲学也有很好的学术传承。 例如刚去世的朱德生先生、更早的熊伟、洪钱等先生也偏重哲学史研究。 相比之下,当时中青代先生重视哲学问题的态度比较明显,如张祥龙先生和陈嘉映先生。 他们并非特别重视哲学史的教育,以陈嘉映老师为例,他在开设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原创课程的同时,开设重视哲学问题的课程,在课堂上抛出他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,引导学生进行讨论。 我认为最好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。 西洋哲学史是一项基本的工作,但研究哲学史毕竟是为了理解和说明这个世界,我认为自己独特鲜明的问题意识是必要的。 我个人的哲学研究还是偏向于问题意识的方向。
哲学与现代社会的过度反思
曾经和澎嘉映先生谈过一些可能引起过度反省的问题。 你自己有这样的体验吗? 这是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吗(思考有自己的局限性,不一定最终能解决问题。 例如,即使彻底研究拖延症也不一定能克服拖延症吗)。 现代社会整体的过度反省体现在哪里呢?
周濂:以休谟为例,他是个平衡感很好的哲学家,他在篝火中思考哲学问题时,成为了怀疑主义者,但当他起床离开篝火时,这些哲学问题就忘了。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,在理论反思与生活实践之间有意识地找到了平衡。 其实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也只是方法论上的怀疑,他明确地说这种怀疑不能应用于生活实践。 为了怀疑而怀疑的话,容易产生过度的反省。 第一次学哲学的人问“为什么”是哲学的怀疑态度,我认为这是对怀疑精神本身的误读。
澎湃新闻:这可能与学生生活经验不大有关。
周濂:的确如此。 学哲学容易成为“发火驱魔”。 如果没有特别充分的生活经验,剑就会变得偏屈,错误地把思想变成世界和生活本身。
澎湃新闻:一些人学哲学的初衷可能是想解决某些问题和困惑。
周濂:是的。 我学习哲学的最初目的之一是理解生活。 哲学没有负责解决这个问题。 “理解生活”是生活本身的问题,而不是思想问题。
澎湃新闻:过度的反省似乎也与现代性有关。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个人问题。 现代社会整体不也有过度反省的问题吗?
周濂:我想我也在。 我在陈嘉映老师及其现代对话中谈到伯纳德·威廉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,他说这是一个全面反省和过度反省的时代,必须彻底反省和追究生活的所有基础。 但是,我认为很多东西是无法追问的。 哲学思维的最初动机是寻找隐性或自明的前提,但其实很多哲学理论和生活实践的前提是给出的,这些给出的不能再三追究了。 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“河床”,它就是基础本身,如果重新审问河床为什么存在,河床背后的支点是什么,陷入虚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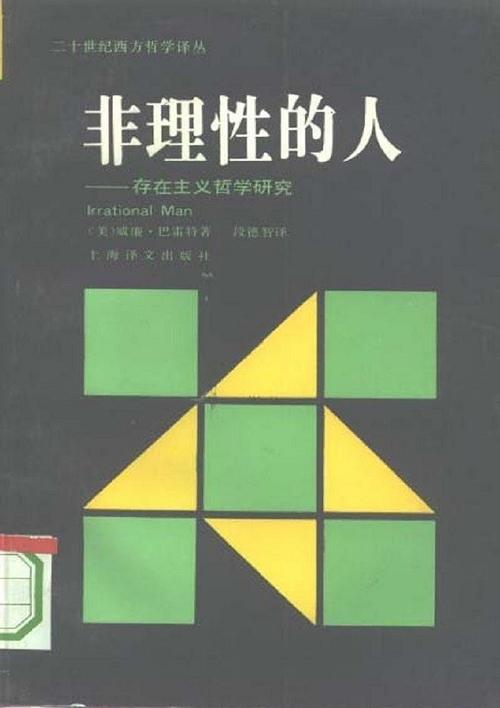
威廉·巴雷特的“不合理的人”
澎湃新闻:苏格拉底所说的“知道你自己”与我们所说的过度反省有关吗?
周濂:苏格拉底想要追究人生是怎样度过的,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人生全体浮现出来,只是让人们去寻找真正的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是什么,并不是否定人生本身。 我们可以从更加世俗的经验角度说“了解你自己”,不一定要提高哲学的高度。 比如说,在这个时代,我们有很多选择和生活的可能性。 我们必须知道“我是谁”,潜力在哪里,兴趣在哪里,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。 我们经常面对的困境是自己不擅长,做着不爱的工作,不喜欢还是不喜欢。 如果不能兼顾,就要作出选择,承担其代价。 我认为“了解你自己”也包括在这方面的选择。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决定,了解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,才能安息在社会和世界中所处的地方,感到收入少于自己的应付,没有怨恨,所以不会对社会的不公平抱怨。
澎湃新闻:但是,在现代社会认识自己比古希腊时代难得多。
周濂:是的。 另一方面,古代社会比我们简单得多,面对的可能性要少得多。 另一方面,古代社会不是围绕着“自由”原则的世界,而是孩子们父子业、阶层的相对固化等,给予了很多东西。 今天的时代完全不同,比如说,出身低矮的人总有一天会成为马云那样的人物。 这至少给了我们上升的希望,但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失落感。 在一个人平等充满机会和自由的世界里,失落感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澎湃新闻:但是,在现代社会,“平等”被视为神,是大家想要的,但现实中有很多不平等,包括家庭和天赐之物。
周濂:当代英美政治哲学,特别是自由主义,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。 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主要来自个人的选择,而不是来自外在的偶然环境,而是来自家庭的诞生和自然的才能。 但是,社会制度能否实现这样的理论承诺是个大问题。 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能力要求非常高,为什么福利国家到今天有点困难,一个原因是理论上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国家履行承诺的能力。
澎湃新闻:在现代人看来,古代社会还很难理解。 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说的线性时间观。
周濂:线性时间观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观,古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循环历史观,历史没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。 此外,我认为威廉·巴雷特的这种观察也很有启发性。 古代社会包含在完全统一的理论中,说明了生活的各个方面,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到我们的日常言行,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都被解释为其理论。 现代社会并非如此,没有不包容的理论,我们的生活是零碎的。 工作只是职业,生活属于完全不同的意义体系,没有任何关联。 这样,生活世界和个体的完整性逐渐消失。 我认为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区别,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有意义的危机问题,特别是不安。 持有宗教信仰的人,被完整性理论包围着,比较安静地生活着。
澎湃新闻:那么你如何评价这两种状态? 我们很难回到过去。
周濂:我想很多人都回不来了。 少数人通过寄身于宗教和特定社区的怀抱,可能会恢复这种完全统一的感觉。 但是,很多现代人回不去。 如何评价古代生活和现代生活的好坏,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 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,现在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多好处,但同时也失去了以前的生活方式所特有的价值。 我常举的例子是恋爱,女孩子总是带着前男友的长处去衡量现在男朋友的缺点,但这种比较不公平,这种比较背后有着一切想法奢侈的愿望。 从一个价值系统到另一个价值系统,交换男朋友,必然要付出代价。 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责任是指出缺点的责任,但没有提供解决方法的责任,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方法。 但是,如果看到缺点本身就能理解的话,达成这个代价和解也是一种更加完善、更加丰富的方法。
澎湃新闻:这种完整性很难理解。
周濂:真难懂啊。 有宗教生活体验的人可能很容易把握。 我亲自阅读威廉·巴雷特的意见时,非常感受到,因为祖父的奶奶是基督徒,所以我也有了直接的生活经验,帮助了他们的理解。
澎湃新闻:提到“完整性”,是否有将自己的人生献给某项事业的人,特别是前辈人很多这种“宗教”的感觉呢
周濂:有。 我有时看纪录片,观察父母,他们有着强烈的献身感,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,也为了祖国的繁荣和高度理想,无论工作多么艰苦,生活环境多么恶劣,他们都有斗志。 之后,包围他们的这个光环消失了,还是有着强烈的丧失感,曾经那个意义丰富的世界远离了他们。 他们必须面对全新的、完全不同标准制定的世界。
澎湃新闻:仅靠收入来衡量自己的工作,有时会失去平衡,很多年轻人会遇到这种情况,尤其是医生这样的行业。
周濂:医学院学生在入学时背诵《希波克拉底的誓言》,誓言给医生这一职业以神圣的感觉,其原本的目的是抵抗世俗的力量,但是这种光线消失后,如果用金钱或别的标准衡量这一职业,当然会产生各种患难的感情。 我认为这是面临这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凉鞋说市场经济很好,但是这个逻辑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话,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。 比如说,人与人之间的温柔并不是金钱的标准,但今天谈到友谊时,也许会用金钱来衡量。 我在朋友圈里见过“什么是真正的朋友”这个词的标准有两个。 一是半夜打电话不受打扰,二是想租一个随时都能说话的朋友。 第二个标准是金钱。
所有职业都有本质标准。 例如,好老师不是赚钱,而是能否传道,好医生的标准可能是救命急救。 但是,我们现在不在乎这些问题,只在乎对方的收入有多少。 这就是受市场逻辑支配的结果。
澎湃新闻:因此,追求这种意义感又成了个人问题。
周瀛:一方面个人化,一方面回到以前所述的问题,健康社会应以不同的逻辑、复杂的方式相互支持,如文化传统、宗教、社区、市场力量相互支持的稳定结构。 但是现在除了政治权力和市场之外没有其他逻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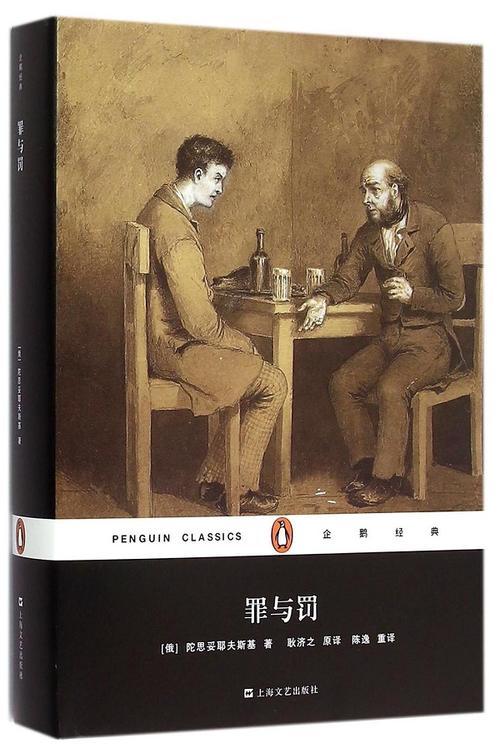
罪与罚
激情新闻:现代社会会变得容易吗? 在前几天陈嘉映老师的采访中说,美国的现代生活变得简单了,比如说很难理解托尔斯泰。 现在的年轻人在心理上比老年人更简单,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变少,多是与自己的“斗争”,比如遇到成长的问题等,会影响伦理学的想法吗?
周濂:关于生活本身,简单是件好事,但关于理论反思和理论建构,简单显然不是好标准。 在这个得失之间不能取得平衡。 看不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意义上是幸运的,他们不需要经历那么残酷的人生,也不需要知道人性的阴暗面。 但是,另一方面,对于能够阅读的人们来说也是幸运的,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和人性本身。 当然,历史越简单,这个国家也许越幸福,但这也许不是人生和历史的真实。 现在西方世界必须重新经历这些复杂和严重,有一天他们的年轻人可能会读这些复杂的文本。